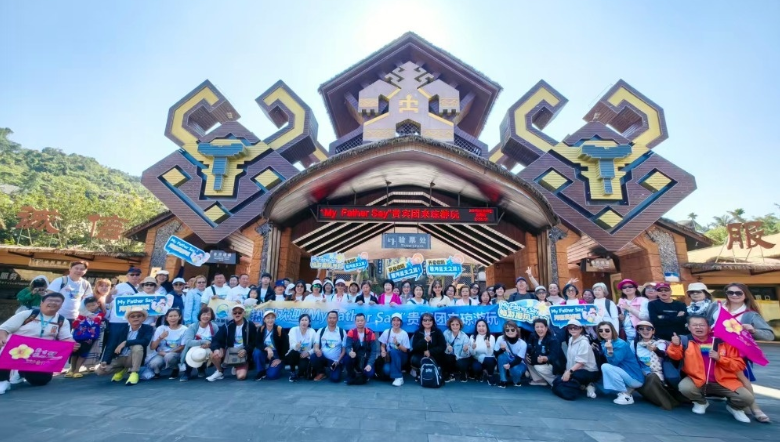海南面向幼儿出版的乡土教材《我爱家乡》中的海南岛地图上,标上了本土的风物特产。


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乡土教材。
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图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以本土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状况等为内容的教材,一般统称为“乡土教材”。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就主张教给儿童乡土地理知识,后来一些教育家把乡土教材逐步扩大到乡土历史、乡土社会、乡土自然、乡土文学等等。
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作品《天涯故事》中曾提到三亚的“鹿回头”。传说中,一头鹿在追捕中奔逃至山崖后突然回眸,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的眼神交汇,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并与猎手成婚。这种深情地回眸,也是余秋雨在文章中隐隐感到的,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文化回眸的目光。
乡土教育正是千娇百媚的文化回眸中的一种。参与编写过海南20世纪初较早一批本土教材《海南历史》、《海南地理》的原海南省教育科学所所长林泽龙认为,从民国以来到现当代乡土教材的传承、推广,既能让海南人文化自觉,也是一次又一次的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等中国多元文化由此及彼、在相互碰撞中相互包容的文化认同。
记忆中的民国教材
随着时间的冲刷,一册册脆弱的纸教材已大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在老一代读书人的记忆中,自民国以来就已有散发着浓郁本土气息的乡土“教材”。
“‘开学了,上学去’这就是一节课了,‘大狗叫,小狗跳’这又是另外一课。”年逾七旬的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谈起过往的乡土教材仍然记忆犹新:“我读小学的时候,都是老师自己用手写的小册子。虽然不算正规,但也是用心良苦。”上世纪40年代,王春煜在琼海的乡下念私塾,由于师资力量缺乏,学习条件艰苦,由教书先生自己编写教材,其目的仅仅是让孩子们从身边的事物中学会认字。“乡下的牵牛花漫山遍野地开,老师就教‘牵牛花开了’。上学的孩子年龄差别大,但是大家都在一起学。”王春煜说。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兴吉在整理史料时,曾发现一本民国时期名为《海南岛游记》的儿童教材,“是一本插图读本,主要是写一位小女孩乘着风伯伯的翅膀,来到了海南。在海南,本地的小朋友请她喝椰子汁,一起做游戏。”张兴吉说,用插图、童话的形式让孩子了解海南,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读本。
“正规装订的教材在民国的时候没有接触到,但是教书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会教一些海南的歌谣和琼剧。”83岁的琼剧作曲家吴梅老人告诉记者,民国时期,关于本土教育多靠教师口口相授,在孩童的好奇心驱使下,无论是在听琼剧中,还是在和来自海南各市县的琼剧演员的交谈中,吴梅都对不同地方的海南话口音和风土人情别有兴趣。
生态文明读本童趣盎然
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婆娑的椰林、没有冬天的海岛,这样的“海南印象”,或许在慢慢地渗入孩子们心中。
“蝴蝶长着色彩斑斓的翅膀,那个是它们自我保护的‘法宝’。有的蝴蝶翅膀上有醒目的花斑,警告其他动物注意:我是有毒的,你可别吃我。”如此充满童趣的语言并不是在讲述某个童话故事,而是适用于三四年级学生的,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编著、三环出版社于2009年2月出版的“生态文明教育”教材。从蝴蝶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开始说起,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谈起海南岛的“蝴蝶王国”:
“海南岛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的蝴蝶种类和数量最多。那里有我国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蝶—金斑喙凤蝶,有我国最大的蝴蝶———金裳凤蝶,它的翅膀展开超过16厘米……”
“我女儿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看完书后时常会问我,海南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动植物呢?五指山真的长得像五个手指吗?”负责该书编写的三环出版社编辑欧大伟告诉记者,该系列丛书共四本,适用于小学和初中。作为海南省九年义务教育地方教材,这也是推动海南建设生态文明示范省的教育实践。“书上会教孩子们椰子的全身都是宝,海南有个美丽的尖峰岭公园,也会引导孩子不能捉鸟蛋,不能伤害海南坡鹿等等。这是让孩子在启蒙时期了解本土文化迈出的第一步。”
“教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林泽龙认为,乡土教材重在“土”,但是乡土教育的对象不应局限在简单地以籍贯划分的“海南人”。从五湖四海来到海南读书的孩子,在共同接受海南乡土教育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认同,一起来热爱美丽的海南岛。
独特的海岛历史文化
林泽龙认为,乡土教育是从本质上弘扬教育,也是从文化视角上认识教育。海南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一方面,中国的三大移民文化“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海南的“下南洋”就占了重要篇章;另一方面,如果将大陆的中原文化定义为“黄土文化”,那么海南也有其独特之处,可定义为“海岛文化”。“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和了解并且认同海南文化,这比任何空谈爱国爱家乡的口号都来得实在。”
林泽龙告诉记者,《海南地理》、《海南历史》两本乡土教材,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多次修订后,一直延续使用至今。记者翻阅《海南历史》一书,以冯白驹的塑像为封面,书中从三亚落笔洞、昌江县霸王岭、皇帝洞开始追溯海南岛的历史源头,其间涉及海南古代经济、古代文化以及抗战中的海南等。
“海南历史很有趣,像黎族古代的社会组织“峒”,都有一个“峒头”,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老大,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和处理一些事务。”海南华侨中学初三毕业学生夏简对海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感兴趣,尽管在考试过程中分值占比较小,但仍愿意在课外花时间阅读。
据林泽龙介绍,本世纪初海南对基础教育进行“课改”后,对教材实行三级管理,分别为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其中,2009年教育部下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明确规定“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和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共占总课时的16%~20%,“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乡土教材有了课时的保障,也可显现乡土教材推动力度之大。”林泽龙说。
目前,已出版的海南中小学生教材有《海南历史》、《海南地理》、《生态文明教育》、音乐教材《椰岛韵律》以及关于安全、环保等方面的专题教育等。[page]

海南乡土教材中对本地蝴蝶的介绍。

《海南历史》对黎锦的介绍图文并茂。

乡土教材《海南历史》内页。
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图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如果以颜色来概括海南的乡土文化,一共是“四色”,你知道吗?
琼州的人文历史和环境资源,不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有了解的必要,对于在这里生长、读书和工作、生活的外地人也有普及的需要,这些常识都会促使新老海南人对这片热土的认同。只有认同,才会深爱。
“苏东坡被贬海南后,进入人生另一个创作高峰。但是,在中小学生的课堂上,又有多少孩子读过苏东坡在海南时写的诗?又有多少人能体会‘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救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的意境呢?”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表示。
通过乡土教材的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海南的乡土文化,走进海南。“以前曾有很多名校的大学生回到海南跟我说,海南缺少文化,这真的让我很痛心。”王春煜说,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力度推广乡土教材,本土教育,但是还远远不够。只有加大力度推广乡土教育,才能踏上海南本土文化的“发现之旅”。
乡土教材推广有难处
王春煜说,海南乡土教材起步比较晚,至今种类仍然不够齐全,尤其在乡土语文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内地有很多城市做得比较好,比如2004年9月浙江出版社出版的杭州市编写的“杭州语文”,共223页,从杭州的风土人情到文人骚客都有涉猎。
在海南出版社的展馆内,记者也看到,除了海南中学生熟知的《海南历史》、《海南地理》,还有其他省份出版的《洛阳历史》、《洛阳地理》、《安阳历史》、《安阳地理》等乡土教材。海南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逸介绍,像河南洛阳、安阳,山东烟台等市县,乡土教材起步比较早,做得也比较好,内容上来说也比海南乡土教材丰富一些。由于教材类图书与普通图书的发行渠道不同,推广起来还需要当地学校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此外,在编写乡土教材的科研力量上也存在不足。
2005年,王春煜曾向海南省教育厅申请,由海南省教育科学院和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联手关于编写《海南乡土语文》的报告,篇目除了古今诗文外,还适当选录了体现海南本土文化特色的琼剧、民歌、楹联等,但后来因资金等多原因搁浅。
王春煜说,茅盾、艾青、郭沫若等人都曾到过海南并写了关于海南的优秀作品。为什么不能选录到语文教材中,开设一门海南乡土语文呢?
不仅是海南乡土语文的推广不大顺畅,作为拥有丰富动植物物种的海南,至今也没有一本在此领域的专门教材。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钟琼芯表示,海南尚未就动植物领域编写过乡土教材,高校的教师倒是发表或出版过相关论文、论著,但由于学术性较强,不宜作为乡土教材推广。他认为,编写出版乡土教材很有必要,有利于向学生群体进行科普教育,让他们了解自己家乡、自己生活学习环境的历史、地理和物种常识。钟琼芯本人曾与海南旅游部门合作,出版过一些有关海南植物的书籍,如《神奇植物》等,对旅游从业人员,主要是导游队伍,起到普及常识的作用。
“四色”乡土文化有待普及
“钓鱼钓到正午头,鱼不上钓心早焦。收起鱼竿回去宅,隔绝不来此路头。”谈到海南本土文化,王春煜教授随口哼起了多年前流行于琼海一带的民谣。“现在这些民谣都极少有人了解,如果不及时整理、保护的话,好多人海南话不讲了、琼剧不听了、民谣也没人唱了。”王春煜教授说,由于乡土教材并不纳入高考考试范围,加上初高中学生目前升学压力大,对乡土教材不够重视。有观点认为海南是文化不丰厚,说明这对海南的文化不了解,也折射出了海南本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自卑。
海南教育专家、原省教育科学所
[page]
马白山将军给女儿的“红色”家书

1951年马白山、唐玲和女儿马洪中(前排右)、儿子合影。

马洪中与母亲唐玲合影。

马白山写给女儿马洪中的家书。
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这是一封长达60多页的家书。尽管并不是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书写,但是这封琼崖纵队杰出领导人马白山将军致女儿的亲笔信,不仅让当时年轻的女儿深谙红色革命精神,也让更多的历史细节展现于后人面前。
7月31日,年近七旬的马洪中在海南省军区白坡里干休所的家里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这位在娘胎里就颠沛流离,生下不久被寄养在农家,直到4岁时才见到父母家人的革命后代,谈及父母,言语中满是敬畏与钦佩。
1992年,马白山将军病危,在病床上给女儿马洪中递了一把保险箱的钥匙。打开这个保险箱,马洪中看到了父亲此前整理的红色革命资料、照片、信笺、手稿……其中有一封长达60多页的信。这封信,是马白山1964年写给女儿的亲笔信,苍劲有力的字里行间,满溢着马白山、唐玲这对革命夫妻对女儿深沉的爱和让人感佩的红色精神。
改名风波,马白山连夜写信
马白山给女儿写的这封信,名字就叫做“妈妈的女儿,女儿的妈妈”,这源于一场“改名风波”。目前,马洪中的母亲唐玲已是103岁的老人,自2009年起便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妈妈这辈子时常怨我,没有跟着她学医”,马洪中边整理老照片边笑着对记者说。1939年3月唐玲参加琼崖纵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的战斗岁月中,一直从事部队的医务工作。“或许也是军医的原因,她做事情总是雷厉风行。”
马洪中是家中唯一的女儿,记者从老照片中看到,这位幼时留着男孩的板寸头、穿着背带裙子扮鬼脸的调皮女孩,背后是父亲母亲对其无限的宠爱。
1964年,马洪中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后,正值大学一年级放寒假,跟随父亲马白山在三亚鹿回头宾馆度假。吃完了晚饭到海边一起散步,马洪中无意中说起:“爸爸,我们的老师同学都说我的名字是男生的名字,能不能给我再起一个女生的名字啊?”在艺术学院里,马洪中是班长还是班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像别的女孩那样拥有一个如梦、浪漫的名字是她小小的心愿,“马洪中”这个有点男性化的名字她并不十分喜欢。但是,马白山听后感到很突然:“不行!绝对不行!”
此时,马洪中才意识到,原来在父亲的眼里,改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父亲告诉我,‘洪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我是在抗日战争的大洪流中、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河边生的。同时也让我铭记我能来到这个世界来之不易,是党和人民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从革命的洪流中抢救出来,从大风大浪中抢救出来,把我培养成人。”马洪中说。
从海边回去后,父亲连夜就动笔开始给马洪中写了这封厚厚的信,叙述了“马洪中”名字的由来,还有母亲唐玲在参加琼崖纵队时十月怀胎的艰辛岁月。
河边出生以草为床
“父亲的字很难认,只有我才认得了。”马洪中拿出当年的书信一字一句的念起来:“‘当时妈妈全然不知道敌人内部的矛盾,还是抱着落难了就准备殉难的准备,为党为国为民殉难是光荣的,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这是爸爸直接用妈妈的口吻给我写的信。”
那是1944年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奉命转战各地掀起反击国民党的高潮。此时,在第二支队担任军医的唐玲将近分娩。原本,支队队长安排两位妇女协助唐玲到附近的山林里“避风头”,但是在躲避国民党地头蛇“搜山”的过程中,唐玲与两位妇女失散了,最终在临高县海孔村不幸被捕。
当时,唐玲被监禁的地方是河边的一个草棚。1944年12月31日晚,马洪中在河边的一个草棚里出生了。不足一平方米的破草棚,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唐玲便急忙趁夜雾未来之前就地收集茅草、树叶,茅草为床,树叶为被,让小马洪中不至于生病。“妈妈又喜欢又发愁,妈妈遭难,你同遭难,妈妈坐牢,你同坐牢,妈妈饥寒,你同饥寒,你的名字怎么叫好,待爸爸给你起吧。”马白山在信中写道。
虎口脱险两入牢房
后来,国民党军队几乎一两天就迁移一个地方,而且全是夜间行军。唐玲抱着小马洪中跟着国民党军队走,有时夜暗路滑,唐玲差点跌倒,小洪中便哇哇大哭。此时,国民党兵就对唐玲免不了一阵毒骂,甚至有人还胁迫她把孩子丢掉。“妈妈特别能忍,我一哭,就用破布塞住我的嘴,渡过难关。”马洪中说道。
1945年2月底,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因调往琼山文昌配合第一支队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离开了临高。此时,常驻村庄的国民党临高县政府及其游击队较少了,唐玲此刻有了同当地群众联系的机会。
唐玲被监禁的地方在临高群白村,与唐玲的姐姐家波莲村离得近,当地的群众对她也熟悉和热情。这是一个让小马洪中“虎口脱险”的好时机。
唐玲对监管她的国民党游击队队长提出:“孩子带在身边,大声啼哭,会暴露目标,影响你们的军事机密。我愿意将孩子送给群众,避免这个麻烦。”后又同一名中年妇女约好,以探村为名,将接应孩子的时间地点告诉唐玲的姐姐。
“我被姨妈姨父接走,他们家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儿子,我们俩人就轮流着喝姨妈的母乳。”但是,马洪中说道,由于姨妈姨父也支持革命,被国民党反动县政府知道后,1948年又将姨父和马洪中送进牢房。数日后,村里的群众卖牛卖地筹了几百大洋,才把姨父和马洪中救出来。
第一次“认识”爸妈
被救出牢房后,琼崖纵队行动在波莲乡附近时的某日上午,马洪中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和母亲,那时的马洪中已有4岁多。
“我不认识爸爸妈妈,经姨妈介绍,我似闻味道一样,一会儿站在妈妈的怀里,摸摸妈妈,一会儿跑到爸爸的怀里,看一看,摸一摸,亲一亲。”马洪中说道,下午了,父亲劝慰了一阵后说道:“你该跟姨妈回去了,等到解放了我和妈妈来接你。”
年幼的马洪中还不知道“解放”的意思,但是她知道,等到那个时候,她就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在日盼夜盼中,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了,姨父笑着对马洪中说:“海南解放了,爸爸妈妈要来接你了。”“我当时立马穿上花衣服,高兴地跳啊蹦啊,觉得马上要和爸爸妈妈一起了。”马洪中回忆道。
同年5月中旬,马洪中在海口的家中见到了哥哥和弟弟,哥哥讲的是昌江话、弟弟讲的是澄迈话,马洪中讲的是临高话,互相听不懂,一旁的妈妈则要充当起“翻译”。幸福的笑声环绕在这个五口之家……
整理史料抢救历史
1992年马白山病危之际,将他最珍视的保险箱交给女儿,保险箱里装的几乎都是将军晚年整理的革命资料。“父亲一直有意识地在做历史材料的整理,这是对历史的‘抢救’。”马洪中告诉记者,说来父亲和母亲态度不一,支持自己考艺术学院也是有“目的”的:他希望马洪中借着艺术的舞台将琼崖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年近古稀的马洪中正在熟练地操作电脑,她告诉记者,帮父亲母亲将琼崖革命的红色精神发扬传承一直是她退休后的使命与责任。“很多人都笑我,说我天天抱着电脑玩,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我是在做一些史料的整理,真的不是在玩。”去年,三集电视纪录片《开国将军马白山》已经开拍,接下来,马洪中正在筹拍讲述父母革命故事的电影《深深的红树林》。[page]